
一个帐篷十二平米,灵车接运放置了三张竹凉床,可供三户人家作为临时避难所。
地震发生后,宜宾长宁县人张书江和女儿以及现在的妻子挤在一张床上,在不安和忧虑中入眠。
6月17日到7月4日,大大小小的余震在四川宜宾长宁县和珙县之间来回蹿动。53岁的张书江5年前再婚迁居来到长宁县双河镇葡萄村,即“6·17”6.0级地震震中。震后,作为丧葬师的他经历了十多年来最为沉重的一次送葬。
口述人:张书江
葡萄村的葬礼
我是五年前来到葡萄村的,带着13岁的女儿跟现在的老婆结婚,她前夫患癌症去世了。她有个儿子,对我挺好的。
我做丧葬生意,村里有四五家在做,大多是年轻人,而我今年53岁,从38岁开始跟着弟弟做这行。唱哀曲、吹唢呐、打鼓、敲锣、写毛笔字、剪纸花等这些技艺,都要学会。每次出外主持丧葬,会持续三到五天不等。赚得多时一个月有3000元,守灵治丧平时就一两千元,能赚就赚点。
在双河镇的这几年,生活还算平静,年年都有小的震动,我都习惯了。只有这次,光我们村就走了5个人。
李家老两口下葬那天,落了好大的雨。(编者注:“6·17”地震中,双河镇葡萄村八组李家祖孙三人不幸遇难。)
他家在高速路交叉口旁,傍晚收费亭灯光亮起,倒塌的房屋大咧咧地垮在那。
小孙子前些日子已经下葬,这次是给老两口送行。一大早天就灰蒙蒙的,走出帐篷,已经有人聚在公路上,商量着去李家送葬的事。我是个丧葬师,这里也称“道士”,这次作为邻居,灵堂租用来为他们送葬。
李家帐篷里有三个“道士”在唱哀曲,宜宾方言伴随着锣、鼓、钹的声音,边打边唱。搞丧葬服务的,看到别人家再悲惨都要忍住,会通过大声唱曲来盖过棺材前的哭声。我坐在帐篷外,主家给我上了一支烟,人多了就摆(注:意为闲聊)起来了。
大概20分钟后,发丧开始,道士念完词后喊一声“出!”8个人就抬着棺材往外走,我和其他人在前面拉,一路要把棺材送上南边的山头。
那会还没下雨,只是雾气重,天也暗。李家的葬礼不像平常那么隆重,但我做丧葬十多年,从没见到送葬的人心情这么沉重。这次地震如果是我赶上了,他们也许是在抬着我去下葬。
大概走了两公里,鲜花灵堂布置棺材抬到了山上。我没休息,下山准备抬第二口。
另一口棺材停在收费亭旁的平地上,就在丧葬师在做仪式的时候,开始落雨了。邻近有个150平米的一层旧瓦房,是个很小的私人酒厂,酒厂前面坝子(平地)上有个红白蓝相间的帐篷,里面好像有病人,做仪式时,医生轻声提示说小声一点。
地震来临时
葡萄村就挨着双河镇所在村,房屋在公路两边,我家在路北侧,屋后是大片竹林。
夏天的葡萄村属于老年人,他们耕种家里的几丈地,喂鸡和猪。闲时看看电视,串门聊会儿天。村里有老年协会,周末就聚在去年新修的村部门口跳“坝坝舞”(广场舞)。他们邀我,遗体告别仪式我不去,觉得不好看。不出门做丧葬时,我就在家看风水相关的书,写毛笔字。
6月17日晚上,天气很热,我坐在二楼中堂的沙发上看抗日剧,女儿躺着玩手机。老婆抱怨电视太吵,我关了电视到隔壁卧室躺下,睡不着就把手机声音开到最小,贴着耳朵听风水相关的网课。
只一会儿,床突然抖了起来,老婆一翻身就跑出门去了。我离门有点远,听到轰隆隆的声音,像放鞭炮一样,隐约还夹杂着玻璃碎落的声音,瓶瓶罐罐跌落的声音,司法鉴定板凳倒地的声音。我把着床,震动感不强。
但我心里很慌,不知觉吼出声来:“我要死了!”想起女儿还睡在中堂,就没想直接跑出去,立马右手抓起手机,左手抓起裤子,想赶紧去救她。当时停电了,震动在继续,我把裤子夹在腋窝下面,右手使劲点手机屏幕,想赶紧打开电筒照明。跑到中堂时,灯光一照床上是空的,女儿应该已经跑出去了。
这时地震停了,我回转头瞥见卧室绿色的床单皱巴巴的,旁边的衣架倒了一地,床头柜被震得离床很远。我拔腿开始向外跑,丧葬用品销售走到楼梯处,台阶上是屋顶掉落的砖块,我是踩着砖块使劲跑下来的,跑下楼之后我才一把穿上裤子。
住在一楼的继子跟儿媳抱着孙女已经出来,老婆和女儿也在外面,老婆见到我就说,岳母还在上面。我和儿子又先后冲进去,岳母是半瘫的人,她抱着门框全身发抖,动弹不得。我和儿子一人抬岳母一只膀子,赶忙提下楼来。一家7口人都到齐了,岳母坐在地上,仍在发抖。
后来开始落雨,女儿、岳母、老婆一起坐在邻居家车后排躲雨。路上还有辆货车,敞开式的车厢上面已经搭起了个棚,村里的女人跟小孩在里面,遗体火化挤满了整辆车。
男人们在外面,大概有几十个,淋着雨,一晚上都没睡。夜里很安静,蛐蛐声音此起彼伏,记不清那天男人之间聊了些啥,我脑子里一直在盘算接下来一家人怎么生活。
回到硐底镇
刚来到双河镇的时候,我谁也不认识,不习惯这里,每天都想回硐底镇。
硐底镇是长宁的,但挨着珙县近。那天珙县也地震了,我就给在硐底镇的弟弟打电话。我俩一起做丧葬服务,十几年了,经常碰面,倒也不怎么习惯打电话。他说不要紧,只是稍微震动。
6月22日,告别仪式珙县又震了,这次更严重,5.4级,打电话过去没人接,我打算第二天过去看看。
23号早上大清早,我骑着摩托从双河镇出来,开上县道,一半的道路上搭了帐篷,路上车也不多。经过龙头镇上了省道,我骑得也不快,60码只要骑半小时就能到,我就一边骑一边看。
路两边都是山,竹子插在斜坡上,两山夹一沟,沟里的人暂时住在红白蓝的塑料布帐篷里。
经过中学时,操场上全是帐篷,人生追悼会等。较为完善的“一条龙”服务体系到处是人,再往前是镇政府,房子没大碍,只是空荡荡的,一个人也没有。
红旗村在硐底镇西边,两面的山一直延伸到珙县。很早的时候,交通很不发达,上学的人也少,村民文化水平偏低。大部分人都去小煤窑打工,煤窑被封后就去采石场做工人,那是最繁重的工作,也有出外打工的。
二十多年前,我离开硐底镇,去外面学习炭精画像,尝试过很多工作,后来也把家里老房子让给了弟弟,他和弟媳修了新房。两间砖砌平房,三面承重墙,预制板结构,屋顶还盖着瓦。经过地震,预制板和砖砌墙之间已经裂开了。
我38岁结婚定居在硐底镇,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入行做丧葬的。那会我在农贸市场附近租了个房,还在市场里开了家店,出售丧葬用品,勉强维持生意。
那天我回到老家的时候,弟弟不在家,我看到弟媳妇跟侄儿、侄女在帐篷里躺着,帐篷是弟媳自己砍了竹子,在旁边搭的。
这里的房子跟葡萄村没有两样,排着震裂的白旧墙壁。弟弟家前面是宗族叔父家,刚修的房子损坏较轻;左边是宗族二哥的老瓦房,已经全塌了,他正搬开瓦喂猪,太危险,我忙叫他别喂了;猪圈前是伯母家,她90多岁了,她家房子是近年来盖的,比较牢固,她躺在屋里的床上,见到我非常激动。
看到亲人都没事,我也就放心了。下午老婆打电话来,喊我回去把家里冰箱挪出来,搬到安全的地方寄放,我也没多停留,骑着摩托返程。
震后生活
余震来的时候,耳边总是轰隆隆的。一到晚上,大家很早就歇下了。夜深以后,田里蛐蛐在叫,在帐篷外走来走去的只有巡逻的人。
“6·17”地震后,我们五组来了9顶帐篷,9~12人住一顶。前一天岳母已被接到镇上的小姨子家,儿子一家去了兴文县未受灾的丈母娘家。我和老婆、女儿三人,与两户邻居总共8个人住一间帐篷,约12平方米。太拥挤,两天后,政府又牵起一个长条大帐篷,离我家房子50米远,里面紧挨着能排十多张床,我就带家人和两张床一起搬进去了。
我们去不远处一家竹器厂买了凉床,好在竹器厂震后仍在营业。床上的铺盖是救灾补给发的,白底上有一个鲜艳的红色“十”字。震后,我上身没有穿衣服,第二天中午便回家爬上楼去,在卧室边上迅速抓了一件黑色上衣,携一个手机充电器就赶紧跑出来了。大夏天,竟抓了一件双层秋衣,我还很后悔没多拿几件。
后来我又进去一次,给老婆和女儿拿衣服。我家的房子一楼顶是预制板,二楼顶才是现浇的。我看到楼上墙壁上有三个拇指宽的裂缝,电脑等很多物件都砸在地上,打烂了。我只是把倒在床头的衣服连着衣架一起抱起,从二楼窗户丢下去,接着就溜出去,一刻也不敢多留。
三餐倒不难解决。开始村民用石头砌灶,捡废木柴烧水,泡方便面吃。不震时,有人进房子取出面和大米,搭伙吃。有人做好饭,看到没吃的,就喊着一块。谁家有锅碗,也借着用。后来政府给每户发了两袋米,一袋大概50斤,还有两桶植物油。
我家门前有几丈地,二十几窝豇豆,四五十窝辣椒,几窝茄子,七八窝还没结的南瓜,与米和油一起,够我们吃上一阵。
目前陆续在修安置房,一户有三人以上的可住入20平方米的安置房,用彩钢顶盖的,胶布绑住墙面,外面围了一圈绿网,像山上竹子的颜色。已经盖起几间了,还没通电,人也还没住进去。20平方米要掏1200元,我不假思索就掏了,帐篷里总归不舒服。



何以为家
7月3日,长宁又地震了,4.8级,比较严重的龙头镇距葡萄村大概只有3公里远,山头都垮了。
那天正是中午,天雾蒙蒙的,山上聚着雾气。
邻居大叔70来岁了,他坐在门前的竹椅上乘凉。我和老婆正跟他聊天,没料到地震来了,我们拔腿就跑到公路空地上。等我缓过神,才见大叔颤巍巍走过来,那时已经震完了。原来上一次地震中他韧带受了伤,几乎无法从竹椅上站起来。
村里大多是20多年前盖的两层楼房,直接由砖块砌成,没有植入钢筋,屋顶直接盖预制板居多,这样的房子禁不起震。
那天,五组村民去队长家里开会,事关震后住宅,每户人都到齐了,我老婆去参加的。听说是政府打算修建住房,需要预先登记购房的村民户数,不过没有一户人家表态。
我觉得,大家并不是担心购房质量,而是不确定购房价格按照商品住房还是灾后安置房标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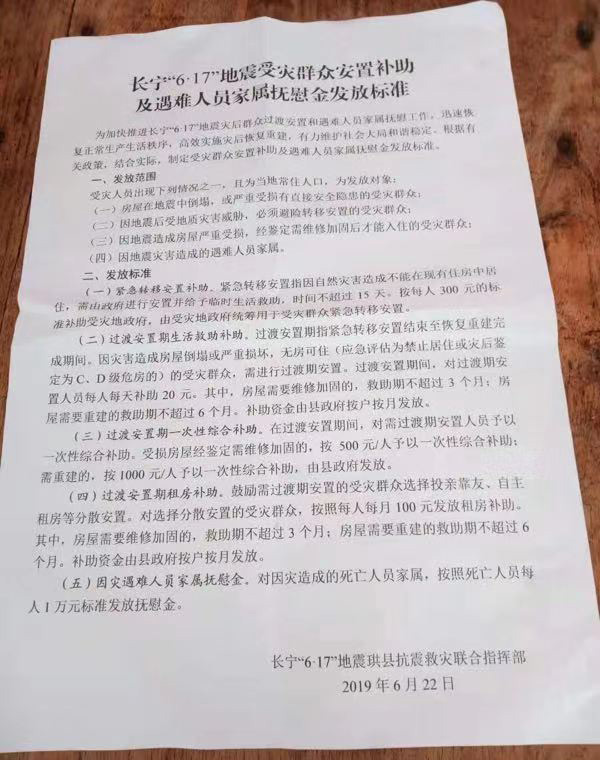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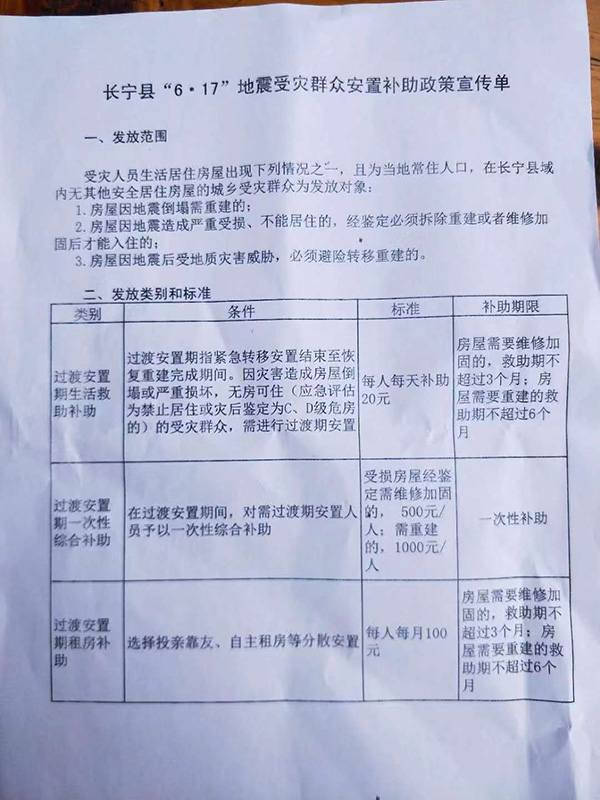
葡萄村是我的第二故乡,但现在的住房必须要推掉,以后不知住在哪里。
老婆已经去竹器厂打工了,一天做10小时,有80块钱,她也捡些废竹料回来,那些竹料会在屋外的土灶里烧得噼里啪啦。
我前几天去镇政府帮忙修建震坏的厨房,挣点生活费。中午回家蒸点米饭,白水煮豇豆,蘸盐吃了,继续去干; 这几日我也开始做丧葬了,一般早上四五点起床,晚上10点才回家。
回来后,老婆和女儿已经睡了,帐篷里亮着灯,邻居有人在聊天。我躺倒在老婆身旁,翻来翻去,很久也睡不着。就拿包烟,装上打火机,出去走。
晚上11点后的村子很安静,路上一个人也没有,隔一百多米有一盏路灯。沿公路向南走,前面丁字路边上的收费亭也亮着灯,上空挂着个电子指示牌,红色的字滚动显示着“天气预报”和“车辆慢行”。走几丈(1丈=3.33米)远,我就折回来,走几个来回。
白天是满的,只有晚上能空下来,看一眼帐篷,就开始发呆,老房子裂了,以后我们一家人到底住在哪里。
走着,熬到眼睛很涩的时候,就回去睡觉,说声“不想了”,第二天还是会想。